
姜文是一位“三少一多”导演:作品少、作品类型少、作品获奖少,作品争议多。自处女作上映起计算,21年时间,姜文总计拍摄了六部长篇电影作品、两部微电影,平均三年磨一剑,即便遭遇如潮质疑,他也从未中断对“荒诞审美”的研究与探索。
姜文是一位“三多一少”演员:作品多、作品类型多、作品好评多、演技争议少。
由此可以大胆假设:姜文熟悉的故事题材多,能驾驭的故事类型多,市场愿意为他承担风险的机会多,但他始终将自己的导演风格锁定在“荒诞”审美上,这是将姜文视为中国荒诞电影最佳代言人的唯一缘由。

同时,在荒诞的表意中,姜文的电影中充分挥洒着生命的野性与张力,在看似荒诞、又混合着暴力腥味的情境中雕刻着活着的意义。
不论主角、配角甚至反派,即便是身处极端荒谬的困境之下,其内心深处都迸发着趋同于《西西弗的神话》中袒露的意念:生命就是如此无意义的荒谬存在,所以更要活下去。
即便巨石(即希望)终究滚回山下(即陨落),人们也要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,找寻到再次出发的动力,并在过程中体尝到意义。

自杀或自我放逐,必将是那些施诅咒之诸神的胜利;坚持并自我注解,才是属于西西弗的个体胜利。这是加缪对世界荒诞性与生存意义的理解,也是姜文电影里展露的生命态度。
生态繁茂图景下的个案补充
先不说姜文的表演作品,单就其1995年成功转型导演后,姜文就成为了“自我隔离”的个案。同时期,中国电影商业化转型已经开始,第五代导演纷纷下场试水,中国港台电影引导潮流,国际交流频繁、市场包容空间巨大。

在如此利好的背景下,多次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姜文越发坚定着自己的艺术判断,没有被商业大片的片约吸引,没急于冲进野蛮生长期的电影市场混战。
那些屡创新高的票房记录无法吸引姜文的关注,反倒是对电影审美本质的探寻、将技术沉浸于艺术呈现之中的创作理念深深刺激着姜文敏锐的五感。他于耳畔听辨出混叠一体的声音层次,他于鼻尖闻到岁月里千人万物的气息,他将过往积累的各色感官,放在了“荒诞”的老窖里,开始酿造他的独特味道。

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(1995)里马小军“主观臆想饭店群殴”的片刻撒欢,到《鬼子来了》(2000)里人性的恣意纵情,姜文越来越娴熟、自信地展现着自己对荒诞审美的理解。即便是遭遇了不同的解读、误读,他始终凝视着电影生态表象背后的“生存逻辑”。
他只想成为自己,一个在生态繁茂的中国电影图景下,特立独行的个案存在。他的“北洋三部曲”在褒贬不一的反馈声中保持孑立,不怒不喜、不卑不亢,任由受众进行表达。
或倾听、或放空,只做选择性回应和必要项解答。此时,受众与市场表达反馈的姿态、情绪、言辞、语汇,都成为了“姜文电影景观”中的一部分。

批判者们可能毫无体察:自己审视、审判姜文电影的同时,正作为姜文电影审美的“被观察对象”之一,以某种荒诞的姿态存在于荒诞审美的批判语境之中。
争论之声越喧嚣,姜文的个案独特性越明确。这是悖论?不,这是对姜文电影荒诞艺术的最好诠释。他确实带着他的思考与作品,成为了电影生态繁茂图景下的独特存在,于电影生态而言,他俨然是一份珍贵难得的个案补充。
形式窄化环境下的自觉独立
荒诞审美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展示了蓬勃生机,在中国荒诞电影、中国讽刺文学和戏剧中汲取大量营养,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构建着自己的艺术骨骼。

但是,不知何时,或许是受到了市场反馈的影响甚或干扰,中国荒诞电影与大量“伴生”概念间相互缠绕,在题材多样化的同时,形式却走向了与魔幻或黑色幽默紧密贴合的窄化路径。
1997年,姜文参演的《有话好好说》中,张艺谋导演和姜文兵分两路,导演在作品的艺术语汇和表现形式上做了大量突破,晃动的手持摄影将生活的荒诞性借视觉外化进行表现,姜文则一本正经、认认真真、执着真诚地表达着实则荒诞的追求。

2002年姜文主演的《寻枪》中,陆川导演和姜文则相互配合,在深沉的镜头凝视中,刻画出马山所陷的失控现实与幻溃精神的双重困境,以及个体在这样荒诞际遇下的无奈与坚持。
此时,姜文在角色塑造上呈现出的信念感,不仅是演员的素养,更是他作为艺术创作者的审美自觉。
随后,姜文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新作,凭借着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和卓越的表演成就,姜文拥有着极大的市场号召力,但这样的人设魅力没能阻止受众对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错愕与反对。

除了随处可查的批评文字或短视频作品,还有一层因素,甚至可谓是这一场批判的底层逻辑之一的因素是,受众潜在得期待“荒诞≈幽默”,“幽默≈好笑”。
从对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批判到接纳,再到奉若至宝的过程里,从多年来的创作窄化生态下的温水青蛙般的习得性认知中,受众对荒诞的接纳前提里似乎总绑定着“好笑”作为“药引子”、“催化剂”。

一部结构颠覆常态时间线、审美荒诞的作品,却居然一点都不“好笑”,这是对观众的极大冒犯和挑战。票房只是市场评估作品和导演影响力的指标之一,但从不是导演对自身审美态度进行审判的唯一标准。
更何况,这一场票房浩劫面对的是姜文,是一个有着自觉力和判断力的思考者。
有人说,不,姜文的《让子弹飞》就是他低头认怂、跟从市场规律的确凿例证。

这部作品不仅回归到“荒诞≈幽默≈好笑”的窄化路线,段子和金句混杂频出,还凭借着几分“狡黠”在审查规则边缘“抖机灵”、恣意蹦跳。
被构图设计消隐的暴力与血腥,一闪而过却一鸣惊人的女配角,充满着不可描述暗示的台词,极尽能事地挑逗着观众的感官神经,甚至激起了观者们压在心底、深藏不可窥探的恶趣味。
但姜文真的向市场妥协了吗?不可能!姜文不过是洞悉了受众的弱点,他换了一种腔调,用一场“真捧杀”的方式,狠狠的打了“市场批评家”们的脸。

用荒诞的刀子,戳破虚伪价值逻辑的包装,并狠狠的向下霍开一个长长的口子。包装里的烂芯子仿佛糠末一般从破口处倾斜流出,但破口的包装袋子却莫名沉浸在“倾泻喷薄”的“畅快”之中,酣快淋漓,自鸣得意。
却不曾留意到姜文经由自己在剧中影像说出的那句宣战檄文:永远不可能跪,这一次要站着把钱赚了,但是咱们不急,让子弹飞一会儿。

在第四十三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,有记者问姜文“拍商业电影是否代表着对观众的妥协”。
姜文从容而明确的说到:
“我从来没有冒犯过观众,我也从来用不着妥协,我觉得想的太多做不了事。你就想拍一个你喜欢的片子,他喜欢了就赶巧就喜欢了,不喜欢呢那就没办法,所以没有人去妥协就有好结果(以上为口语原文,意译为“没有人因为妥协而得到好结果”)”。
这段采访在网上被广泛转发,姜文在参加央视《面对面》栏目时坦言到:希望自己能做尊重观众的导演。他最大的本分,就是把作品拍好。他希望别人看到的是姜文对电影的热爱。这些毫无掩饰的话语恰是姜文的电影创作观念。

这与这个世界大多人看到的趋同现象不同,因此,人们假定了姜文的孤独甚至孤立——这种评价是无源之水的臆想,秉持这样观点的人,不就是姜文电影《让子弹飞》里那些赤膊持枪的盲从群体吗?
站在影视批评的语境里,大多数人都认同这句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和“站着赚钱”是读懂《让子弹飞》的两把钥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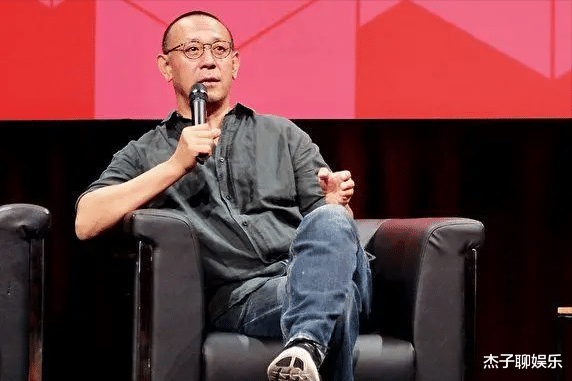
但,站在当代艺术的视域中,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产品,更是一件沉浸式的行为艺术作品:将作品内的故事空间和外部的观影空间集结在一起,构成完整的审美场域;将作品内的表意符号与外部观影者、批评者圈为一体,共同成为审美对象。
此时再品咂这两句话,大概率会体会到这两句话共同构成了一张标签,清晰的标注着这部作品的创作意图:
把“你”拉进鹅城,一起扮相,一起演戏。但“你”是否知道。一会儿看到“笑料”时,最好忍一忍,让子弹飞一会儿,看看到底击穿了谁的面具!黄四郎是角色,也是某些不知自的观者;

马邦德是剧中的个体,也是某些沾沾得意的群体。而大多数人都将自己代入张麻子的视角,审判着鹅城的荒诞,倾情嘲讽剧中的“小丑”。
而这,才是《让子弹飞》所审视的荒诞与错位:观者在剧场里拍腿笑着故事时,故事里的张麻子再淡定的凝视着观者,并微微点头,表达鼓励。剧中的角色或许都看到了“子弹飞一会儿”的结果。

观者的列位却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曾应验过一句网络流行语: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曹先生的金句或许只有放在“悲怆 幻灭”的故事里才能被人感知。
荒诞故事创作的核心是搭建错位的情境与异化的关系。在这个多味元素混杂叠化的时空里,审美与被审美者悄然交换了身份。
但总有人以为自己身披铠甲,却全然不知那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,而他自以为的气宇轩昂、挥斥方遒,只是一派“贾雨村言”。

这,才是真实的荒诞。再看剧中张麻子,面对荒诞的一切,他所坚持的只是以退为进的“戴上面具”(消解表达自身存在的符号),只是拼尽全力的“站着”(加缪西西弗式的坚持)。
在众人的狂欢笑声中,姜文以冷峻凛冽的姿态,秉持着自己的审美自觉,完成了加缪式荒诞审美在国产电影创作中的探索实验与铿锵表达。
北洋三部曲的后两部中,姜文将自己对荒诞审美的理解与追求被发挥到淋漓尽致。姜文把“错位”的荒诞浸润在对立共存的细节中。

比如《一步之遥》中乱世与繁华的戏剧情境,虚伪与真诚的矛盾人性,保守与变革的不同群体,卑微与觉醒的个体存在。他把“异化”的无奈雕刻在角色的血脉里。
比如《邪不压正》中,李天然情感上的仇恨与怯懦交融、身份上的杀戮(杀手)与拯救(医生)并存;朱潜龙人设上的拼贴虚构的“伟大使命”、立场上摇摆不定的“坚定不移”……这些明晃晃的设计,被观者们一眼识别并怡然自乐,嚼出汁来,或品或唾,分享着自己睿智观察的成果,各得其味。
但这些设计背后的底层逻辑,则依然是将“评论者”圈入“评论场域”的悖论荒诞。评论者们是诸神,姜文是西西弗。诸神以自己的“权力”与“魔力”施于西西弗“终生推石”的诅咒。

却不料,西西弗在循环往复的虚无中,修成了参透生命本意的正果。《西西弗的神话》里的悖论与荒诞、毁灭与自觉,为姜文的作品做着注解。无论环境如何窄化,姜文始终秉持着审美自觉:
用通俗语汇讲一个浮华精彩的故事,用审美态度刻一枚内敛宏大的寓言,在表象与内核的错位空间里,在异化角色的荒诞境遇中,大家对号入座,各取所需。
姜文,在不远处,微笑凝视。




